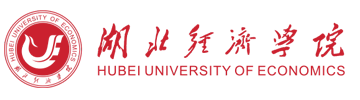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围绕犯罪客体问题正在进行深入的讨论。下面,我想就讨论中的一些问题谈谈管窥之见。
一、关于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一个要件的观点,是否肇始于前苏联学者
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有些学者持肯定意见。例如,《刑法教科书》的作者指出,“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对资产阶级的犯罪客体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把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并且认为犯罪客体不是法益而是社会关系。”① 另一位学者表述的更为明确、具体,他指出,“前苏联学者对大陆法系的上述犯罪论体系进行了改造,将上述成立犯罪的三个条件转变为犯罪构成:构成要件被改造为犯罪客观要件;实质的违法性被改造为犯罪客体;有责性被分解为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于是形成了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说。”②
如何看待上述意见?我认为,这些结论性意见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据文献调查,在前苏联学者之前就有人将犯罪客体视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或“四要件”之一。例如,沙俄著名刑法学者А•季斯嘉科夫斯基教授曾把犯罪行为不可缺少的必要要件称为犯罪构成。“这样的要件有四个:主体、客体、主体的内在活动和外在活动以及活动的结果。”③ 需要说明的是,这段话源于俄罗斯当代著名刑法学者Н•库兹涅佐娃关于俄罗斯犯罪构成学说的历史回顾。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最具影响力的刑法学家Н•塔甘采夫教授也把犯罪行为固有的要件的总和称之为犯罪构成。以此为逻辑起点,他在犯罪构成中划分出三个要件(要素):a,行为人——犯罪人;b,犯罪人的行为所指向的事物——犯罪客体;c,从内部和外部研究的行为本身。④ 这里所说的作为犯罪人的行为所指向的事物的犯罪客体作何理解?它是指犯罪客体还是犯罪对象?Н•塔甘采夫对此写道:“当把犯罪行为界定为对法律所保护的生活利益的侵犯时,我们就确立了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概念。客体是准则或法的规范,即在主观权利范围内获得保护的生活利益所体现的准则或法的规范。例如,说盗窃是窃取他人的动产,我们进而指明,犯罪行为指向的具体对象是处在某种拥有的表、钱包,而抽象的客体则是决定人对财产关系的法规范和被保护的所有、占有的不可侵犯性。”⑤ 这段论述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Н•塔甘采夫所说的犯罪客体是指“在主观权利范围内获得保护的生活利益所体现的准则或法的规范”,而不是指犯罪对象,并且它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
应当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关于犯罪构成究竟由四个要件或三个要件组成在俄国刑法学者中尚未形成共识,但将犯罪客体视为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却非个别之见。由此笔者的结论是:在俄罗斯刑法史上,最早提出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的不是苏维埃学者。毫无疑问,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是在批判吸收资产阶级犯罪客体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起来的。但需要明确这里所言的资产阶级犯罪客体理论主要是指俄国的犯罪客体学说,其理论源头是德国早期的刑法理论。贝格林——麦耶尔创立的犯罪论体系于20世纪20年代才在德国成为具有统治力的理论,当时的俄国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何秉松教授说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并未受到贝格林——麦耶尔的理论影响”,⑥ 我认为是可信的。实际上,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并不是对大陆法系“三要件”理论体系直接改造的结果。
二、是否应将犯罪客体置于犯罪构成之外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的学者对于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犯罪行为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反映的是犯罪行为的实质,这正是犯罪概念所研究的对象,没有必要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马克思所说的“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在于侵害了某种物质关系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恰恰揭示了犯罪本质,而非犯罪客体。⑦
前述观点因其新颖性和独创性而受到刑法学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和对德日构成要件理论了解的深入,对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的观点说“不”的人多了,声音也大了,其代表人物张明楷教授。他对“法益不是构成要件”作了全方位、深入的论证,主要论点有:其一,犯罪客体说明的是,犯罪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法益。但是,犯罪概念首先揭示了犯罪的本质在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侵犯了法益,或者说是犯罪行为对特定法益的侵犯性。显然这里的法益不是抽象的,而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可见,犯罪客体的意义已经被包含在犯罪概念之中。其二,犯罪客体本身是被侵犯的法益,但要确定某种行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了什么样的法益,并不能由犯罪客体来解决;从法律上说,要通过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综合反映出来;从现实上说,要通过符合上述三个要件的事实(犯罪构成事实)综合反映出来。其三,主张犯罪客体不是犯罪构成要件,是否会给犯罪的认定带来困难呢?不会。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法益,是由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与主观要件以及符合这些要件的事实综合决定的;区分此罪与彼罪,关键在于分析犯罪主客观方面的特征。⑧
首先,笔者对犯罪客体是“犯罪概念所研究的对象”、它的“意义已经被包含在犯罪概念之中”的观点不持异议。依照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其本质属性之一是社会危害性。这种属性是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等直接相关联的。这说明犯罪客体是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首要因素。在犯罪概念中研究犯罪客体,有助于揭示犯罪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危害性的结构。
另一方面,不同于前述论者,我认为犯罪客体具有双重品格、双重意义⑨,即它的意义不仅“被包含在犯罪概念之中”,而且也被包含在犯罪构成概念之中。犯罪是复杂的社会法律现象,除了其本质属性外,还有自己的构成要素(要件)和结构,即犯罪构成。在犯罪构成中,犯罪客体作为一个构成要件是同犯罪主体、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发生联系的,并且犯罪构成的整体性及性能也就存在于它们的联系之中。既然犯罪客体参与了犯罪构成这个有机整体及其性能的形成,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就应当承认它的意义已被包含在犯罪构成概念之中。应当指出,在犯罪构成概念中研究犯罪客体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于在犯罪概念中研究犯罪客体。前者是把犯罪客体视为一个构成要件,后者是通过研究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害性,即社会危害性进行的。尽管如此,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⑩。
以上解读的根据是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其方法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主客观相统一的思想,即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意识的统一。德日两国的构成要件论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嬗变的过程,它的方法论基础也不同于我们。但到了后贝林格时代,德日两国构成要件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例如,贝林格认为,“构成要件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也就是说,构成要件是刑罚法规所规定的行为的类型,但这种类型专门体现在行为的客观方面”(11),与主观要素无涉。20世纪30年代,日本著名学者小野清一郎把构成要件的内容修正为“违法并且在道义上有责任的行为类型”,“所以,其中当然包含有主观要素”(12)。这里所说的主观要素,是指作为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的故意和过失。前者只包括“对犯罪事实的认识”,后者只限于“客观注意义务的违反”。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刑法学者日趋关注法益(犯罪客体)问题。在这种氛围下,德国著名刑法学者汉斯•耶赛克与托马斯•魏根特主张法益是构成要件的一个构成要素。他们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指出,“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是通过对构成相关犯罪种类的不法内容的特征进行概括而产生的。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有法益、行为客体、行为人、行为和结果。通过这些构成要素结合成构成要件,立法者使得规范命令简洁明了”。(13)
汉斯•耶赛克与托马斯•魏根特两位教授关于法益是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的观点在德日等国的影响力如何,我不敢冒昧加以揣测,但它至少否定了国内有的学者的结论,即大陆法系国家“没有任何人主张法益本身是构成要件要素”,“法益问题一直是在犯罪本质或犯罪概念层次讨论的,而不是在构成要件的层次上研究的”。(14)
其次,在我国“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15) 在这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犯罪客体虽然是“被侵犯的”、“被动的”,但它也具有认证价值。从法律上说,犯罪客体是一个构成要件,它是否受到侵犯,不仅要去考察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也要看看犯罪客体本身。从现实上说,侵犯与被侵犯是一种客观事实,自然应当包括被侵犯的客体事实。
最后,在犯罪的认定上也不应该抛开犯罪客体。犯罪的认定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区分罪与非罪;二是区分此罪与彼罪。就第一种情况而言,离开了犯罪客体,就无法正确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里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要确定后者,犯罪客体应是首先考虑的要素。在区分此罪与彼罪时,虽然更多的是在分析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但客体要件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例如,轰动京城的刘海洋用硫酸伤害黑熊案。在讨论过程中人们有不同意见,最后达成共识:刘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之所以如此,除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外,还在于黑熊是动物园的财产,用硫酸伤害黑熊,就侵犯了动物园对它的所有权。显然,在类似的场合也不应该冷落犯罪客体。
把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有助于司法机关根据犯罪的法律属性来认定犯罪。否则,就会在认定上给司法人员留下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我们知道德国是法益理论的发源地。在魏玛共和时期,曾发生法官拒绝审判镇压、杀害工人的事件,理由是法益处在构成要件之外和法益没有受到侵害。(16)
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的理论框架和构造形态虽是从前苏联移植来的,但经过国内几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具有中国特色,并且适应了我国刑事立法和审判实践的需要。贸然改动成本过大,没有必要。因此,否认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一个要件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
三、用法益或社会利益取代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是否为一个与时俱进的选择
法益(法所保护的利益)说滥觞于德国,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与完善,已成为德国、日本等国的通说。
用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始于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苏维埃学者А•皮昂特科夫斯基在其撰写的《苏维埃刑法总论》(1924年)、《苏维埃刑法分论》(1928年)中,首次提出“把犯罪客体看作是某个具体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新观点。是什么原因促使А•皮昂特科夫斯基主张用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呢?就宏观层面而言,任何理论都是一定的社会的产物,即“人们实际生活进程”的反映。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是它的主要矛盾。苏维埃俄国所经历的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便是证明。20世纪20年代,疾风暴雨式的武装斗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意识形态领域内“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为此,俄共(布)开展了“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而进行的斗争”。А•皮昂特科夫斯基教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考察刑法问题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从具体层面看,А•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其一,依据德国法学家耶林的法的一般理论所建构的法益论,不能提供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犯罪客体的真实概念,用法益作为犯罪客体实际上是掩盖了资产阶级刑法的阶级本质。而社会关系则是在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把社会关系看作是保护的客体,可以凸显刑法的阶级性。
其二,把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源于立法上的规定,存在立法上的根据。1919年《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在界定刑法时指出,“刑法是用来保护本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制度,以制裁方法(刑罚)来制止违法行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及其他法律措施。”该原则第3条还规定,“苏维埃刑法的任务,是用制裁的方法来保护符合于劳动群众利益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劳动群众就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所组成的统治阶级。”从上可以看出,立法明确地将社会关系规定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即犯罪客体。
其三,把犯罪客体理解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同犯罪的实质概念密切相连的。1922年《苏俄刑法典》提供的就是犯罪的实质概念。依照刑法典,犯罪是威胁苏维埃制度基础及工农政权在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时期所建立的法律秩序的一切危害社会的作为或不作为。这里,犯罪的社会属性是同作为社会关系的苏维埃制度基础和法律秩序直接相关联的,即犯罪的社会属性取决于对社会关系的侵犯(17)。此外,把犯罪客体理解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也符合马克思的论断:“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
А•皮昂特科夫斯基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法益论和论证自己的新观点时,都是以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苏俄立法为依据的,其出发点是建构不同于“虚伪的法益论”的犯罪客体新理论。А•皮昂特科夫斯基教授关于犯罪客体的新观点得到苏维埃刑法学者们的广泛赞同和支持,成为“苏维埃著作中公认的一个原理”。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传入我国,并被我们无保留地接受下来。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进行反思。《刑法教科书》的作者认为,“把犯罪客体仅仅归结为社会关系,而把生产力和自然环境排除在犯罪客体之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18) 基于此,前述作者主张用社会利益或法益取代社会关系。因为利益是一个含义深刻、内容丰富的社会范畴。(19)《刑法教科书》作者的前述观点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所支持,认为它“具有合理性”(20),但也有一部分学者继续坚持“社会关系说”。
理论的命运总是同历史的进程密切相连。每当社会历史处于转折关头或变革时期,原有的理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或者被取而代之。法益说、社会关系说、社会利益说或法益说的“轮回”便是证明。我们知道,А•皮昂特科夫斯基教授主张用“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取代“法益”作为犯罪客体的一个重要根据在于,“法益说”掩盖了刑法和保护客体的阶级本质。因此,以彰显刑法和保护客体的阶级属性为特征的“社会关系说”就适应了前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初期的需要,并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自上个世纪30年代末起,苏维埃社会先由阶级社会转变为不以阶级对抗、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后来又发展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结构、社会条件变化了,但犯罪客体理论没有与时俱进,几十年几乎一成不变,脱离了变化的社会现实。
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接受前苏联的犯罪客体理论,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最主要的是它适合我国的当时国情。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以彰显刑法的阶级性为内容的“社会关系说”难以与时代主题契合,不利于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实现全社会公正的要求。这是我赞同以“法益说”取代“社会关系说”的重要原因。此外,传统的犯罪客体概念也确实存在批判者所指陈的先天不足的缺憾,如涵盖面窄,不能把一切犯罪客体包容在内等。
四、国家安全、公民权利、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是否为一种利益
法益离不开利益。何为利益?它的实质是什么?这是些见仁见智的问题。仅就我国哲学界而言,就提供了多种殊有分歧的利益定义。不过,这些界定之间也不乏共同点,如从需要出发来界定利益,认为需要是利益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利益不直接就是需要,也不直接就是满足需要的对象,它必须以社会生产关系为中介,即社会关系是利益的社会基础;利益的内容是客观的,具有客观性;利益同人们的实践活动相联系。
我们认为,利益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它反映的是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存在的一种矛盾关系。因此,不能把利益理解为某种实物或物品;否则,就是把利益对象等同于利益本身。这一点对犯罪客体理论尤为重要。它既是区分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否定主张保留犯罪对象(行为对象)、取消犯罪客体作为构成要件的观点的根据。
其次,利益虽然是一个关系范畴,但它反映的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却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指出,“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21)“利益是讲求实际的。”(22) 应当把利益与对利益的评价区分开来,尽管两者密切相关,但对利益的评价绝不是利益本身。所谓利益就是“好处”的观点以及所谓利益就是“需要的满足状态”的观点,“是把利益看成了一个指涉利益主体主观感觉状态的概念,其实质是把对利益效果、功能的评价当成利益本身。”(23)
最后,利益是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存在的一种矛盾关系。利益是由需要引起的,后者是利益的自然基础和前提。没有需要也就没有人对需要对象的依赖和占有,也就没有需要主体和需要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界定利益离不开需要。但是,需要本身并不就是利益,利益是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存在的一种矛盾关系。只有当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时,需要才转化为利益。反之,需要就是需要,它不会转化为利益。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人们对空气和生态环境的需要并不会转化为利益。但是,当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呼吸新鲜空气变得异常困难时,人们对清洁空气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就成了他们的利益所在,立法者才用刑法对其加以保护。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即利益只有在有对立的地方才存在(24)。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需要与需要对象之间的矛盾关系都是利益,只有当这种矛盾关系是在社会中由群体生活所造成的时候,它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利益。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同:利益的实质“是社会化的需要,即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25)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利益“内容广泛,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无论侵犯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或自然环境,都可以归结为对社会利益的侵害。”(26) 总的讲,这个结论并不错。但问题在于,我国刑法第2条、第13条规定的保护客体是国家安全,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等。这些保护客体并不直接等同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或自然环境。对前者的侵犯归结为对社会利益的侵犯,还需要加以论证,即证明国家安全、公民的权利、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为利益。
我国刑法明确把国家安全规定为保护客体。它是否是一种利益?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从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动机出发,把安全看作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哲学意义上的需要,是人们对于外界对象的依赖关系。需要与利益既一致又有区别,但需要本身不是利益。利益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存在的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利益与需要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它具有社会关系的本质。因此,只有以社会关系为中介,需要才能转化为利益。
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国家安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综合安全。具体表现为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受侵犯等。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已不是纯而又纯的需要,而是通过法律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即利益。
刑法所规定的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是否为一种利益?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利益说认为,权利就是利益。也有的学者认为,利益与权利不是等同的概念,前者的外延比后者的外延要广一些(27),但该学者没有说明在两者重合的场合,权利是否就是利益。
一般而言,权利不直接就是利益。例如,在一定的社会里,当某个主体的权利不被承认时,其利益并不因此而消失。此外,当一个人因主观原因或客观原因暂不能行使其权利时,他的利益仍是一种客观存在。例如,对于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来说,他暂时不能行使其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丧失了为了生存和发展的相关利益。从这样的视角观察,权利只是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而不直接就是利益。
如果转换视角,从刑法角度进行分析,上述结论就会发生逆转。理由是:
其一,刑法所保护的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源于宪法的规定,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法定性,对这些权利的承认与保护,不以他人、群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易言之,刑法上的权利同相关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分离的。
其二,尽管法学界对权利的表述纷繁多样,但我们认同这样的界定:权利是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由其他人的法律义务所保证的法律手段(28)。该定义表明,利益是权利的目的,权利是实现利益的手段。权利之所以成为法律手段,就在于它对人们实现其利益具有一定的有用性,即工具价值。既然权利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利益的手段,那么,权利本身在法律关系中也是一种利益。
社会秩序也是我国刑法的保护客体。一般言之,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有序状态,其表征是社会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社会结构的均衡性和社会行为的有规则性。社会秩序是否是一种利益?大陆学者对此鲜有论述。我国台湾学者苏俊雄将社会秩序和利益并列起来,认为刑法的机能包括维持社会秩序、制裁即防止犯罪、保护法益及社会伦理的行为价值(29)。将社会秩序与法益并列起来,说明他们互不包容。按照苏俊雄的观点,法益显然不包括社会秩序。日本学者内藤谦认为,如果说维持秩序意味着维护社会的有序状态,进而保护社会成员的生活利益,应当作为法益加以保护。而且,维持秩序一语,所重视的不是对社会成员的生活利益或法益的保护,大多强调的是对现存的社会秩序、整体状态的维护,故不宜将法益包含在秩序概念中,当某种秩序属于社会成员的生活利益时,将这秩序归入法益较为合适(30)。内藤谦的观点是二元的。一方面,他主张秩序属于社会成员的生活利益;另一方面,又认为维持秩序所固有的内涵是同社会成员的生活利益相抵牾的。
我们认为,如果社会秩序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恰当表现,客观地体现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那么,这种秩序不仅是利益的前提,进一步看,秩序本身也是一种利益。秩序和维持秩序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没有维持就没有秩序。从理论上讲,秩序(社会秩序)的本质是强调人们行为的规则性和有序性,使其行为朝着功能确定、整体协调的方向发展。而维持秩序的侧重点则是把意识彼此不同、利益复杂多样的社会人群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使他们的行为既千差万别又符合社会的要求而不发生“越轨”。尽管两者的侧重点不同,但就其本性而言,维持秩序同社会成员的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存在着一种有机的、相互包容的关系,因此,把维持秩序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对立起来并非妥当。当然,只有维持“糟糕的秩序”才是同“社会成员的生活利益”相抵触的。
从我国刑法分则第6章看,社会秩序的范围较为广泛,它包括公共秩序、司法管理秩序、国(边)境管理秩序、文物管理秩序、公共卫生秩序等。这些秩序具有共同的属性,并且在这种共同属性方面彼此是等价的。刑法将这些秩序作为利益加以保护,说明它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
市场经济秩序是秩序的一种,因此,它同利益的相互关系也适用于社会秩序与利益之间的相互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秩序同利益具有更密切的关系。因为一定的市场经济秩序总是作为维系相应的经济利益格局而存在的。经济利益的任何调整和变动,都将导致秩序状态的变化。我们认为,稳定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看作是一种利益符合我国的实际。
本文原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6期
【注释】
①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②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③[俄]Н•库兹涅佐娃等主编:《俄罗斯刑法教程》(上卷•犯罪论),黄道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④参见[俄]Н•塔甘采夫著:《俄国刑法》(总论两卷本)第1卷,俄罗斯图拉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页。
⑤[俄]Н•塔甘采夫著:《俄国刑法》(总论两卷本)第1卷,俄罗斯图拉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页。
⑥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⑦参见张文:“犯罪构成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
⑧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1页。
⑨参见薛瑞麟著:《俄罗斯刑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⑩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11)[日]小野清一郎著:《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2)[日]小野清一郎著:《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13)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14)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第157页。
(1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16)参见[前苏联]А•皮昂特科夫斯基等主编:《苏维埃刑法教程》(第2卷),俄罗斯科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30页。
(17)参见[前苏联]А•皮昂特科夫斯基著:《苏维埃刑法中的犯罪学说》,俄罗斯法律文献出版社1961年版,第132页-第137页。
(18)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19)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20)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页。
(23)张玉堂著:《利益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24)张玉堂著:《利益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25)《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页。
(26)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27)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28)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29)转引自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30)转引自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